时间:2023-04-19 23:36:58来源:法律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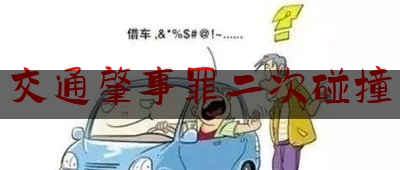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4日晚,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西大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程某驾驶出租车由西向东行驶,将欲横穿马路的行人王某(72岁)撞倒在地后逃逸。由于年纪较大缺乏自救能力,王某只得坐在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招手警示。程某在逃逸后,两次返回现场观望,但并未下车实施救助。在其第二次返回时,发现王某已被碾压。肇事者为保时捷轿车司机黎某,司机已逃逸。随后王某被群众发现,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起初,黎某推出其父亲、婆婆顶包,被警方识破后自首。经查明,黎某系无证驾驶。
公诉机关以被告人程某、黎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本案现在已经宣判。
二、本案出租车司机程某的行为如何定罪
(一)意见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出租车司机程某的行为如何定罪,存在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程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交警部门认定程某和黎某共同负事故全部责任,二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均未保持行车安全,肇事行为均具有独立性,是两次独立的事故,且案件发生后两人均有逃逸行为,最终造成受害人死亡后果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致一人死亡的,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分别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程某只是将被害人撞伤,之后黎某的行为才致使被害人死亡。黎某原因力介入因素足以阻断程某肇事行为与死亡后果的因果关系,故黎某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而程某的行为不具有刑法上评价的意义,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二)法理分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作如下分析。
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过失犯罪只存在罪与非罪,不存在预备、中止与未遂之分。一般来说,发生在公共交通的范围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定交通肇事罪而非过失致人死亡罪。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程某实施了交通肇事的实行行为,其中又有黎某二次碾压的介入因素存在,这一介入因素是否能阻断程某成立交通肇事罪。
我国现行刑法通说理论认为,因果关系的介入因素是指先前实行行为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过程当中,介入了第三人行为、被害人行为、行为人的第二次行为或者自然事件,从而引起因果关系可能发生异常变化情况,即先前实行行为→介入因素→危害结果。介入因素是否阻断先前实行行为的因果关系,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1)先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概率的大小。先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概率的大小只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中断的一个方面,概率大并不必然不中断。(2)介入因素是否异常。所谓异常,指通常情况下不会介入的某种行为或自然力。如果介入原因属于通常介入,则不能中断因果关系。(3)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如果先行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极大可能性,后续的介入因素只是起到一个推进作用,即就算具体的死亡是由介入因素直接导致的,也应归责于先行行为,视为先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笔者认为,在判断介入因素的异常性,或者先行行为与介入因素的关联性时,不能孤立地判断,而应当进行情景化判断。
涉及到本案,案发时间是下着雨的夜晚,行车视野不清,程某撞击被害人后,理应停车报警,积极实施救助义务,但是其选择了逃逸。而被害人年事已高,被撞伤后已无法行动,程某将其置身于车流密集的机动车道上,周围车辆川流不息,随时有可能再次受到伤害,或者说,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程某此时的主观意图已经不是原来交通肇事时的过失,而是对被害人的人身有可能进一步受到损害的听之任之,存在放任的主观态度。
尽管事发后,被害人尚能向来往车辆挥手示警,但是从一般常识分析,在未得到及时救助的情况下,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在车祸中受到严重撞击后生命体征是会逐渐消亡的,未当场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定不会死亡,被害人最终的死亡结果可以说在程某的可预期范围内。此后,黎某驾驶小轿车在城市公共道路上正常行驶,面对被程某遗弃的不能动弹的被害人,黎某疏于注意义务而发生了碾压事故。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即使不是黎某驾车驶过,也可能会发生其他司机驾车碾压被害人的后果。
综上,程某先前的肇事行为对引起死亡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极大,而黎某的肇事介入因素不属于异常因素,其碾压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可能性不超过正常人的预期范围。所以,笔者认为,本案即使存在黎某肇事的介入因素,也不能阻断程某的犯罪成立,程某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论处。
三、本案保时捷司机黎某的行为如何定罪
(一)意见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保时捷车主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也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现场摄像头监控资料显示,被害人跌坐在马路中央且挥手示警,来往多辆机动车均减速绕行,黎某却无证驾驶撞向被害人,其主观方面存在间接杀人的故意。
第二种意见认为,黎某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案发时,黎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也未经过正规严格的培训,对交通规则不熟悉,驾车技术不熟练,这些都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黎某放任自己无证驾驶的行为会对社会秩序和他人的生命健康造成现实紧迫的危害,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黎某的行为仍构成交通肇事罪。黎某撞倒被害人主观上是出于过失,而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找人顶包等均是本罪的从重处罚情节。
(二)法理分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作如下分析。
1、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
首先,黎某主观不存在杀人的犯罪故意。在交通肇事案件中, 通常会将行为人有意识地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理解成为“故意”, 但这种“故意”是违反交通法规的故意,而并非杀害被害人的故意,肇事者对被害人伤亡时持有的心态应当是过失。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如果是使用车辆杀害被害人,则行为人需要有意识地将车辆作为杀人作案的工具使用。本案中,黎某与死者王某素不相识,没有任何矛盾纠纷,缺乏杀人的动机。黎某虽然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她认为凭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不会发生事故,其“故意”的心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证驾驶的违法故意。当晚黎某驾驶机动车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交通工具而非作案工具,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没有抱有任何预料和期盼。案件发生在夜晚而且下着雨,黎某驾车行驶时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而撞上跌坐在马路中央的老人王某, 但她其撞人后立即靠边停车,并下车查看王某的伤势情况。这一系列行为反映出黎某肇事时并未持有希望事故发生、放任事故发生的主观态度, 对被害人王某的死亡其内心是否定和排斥的, 是一种事与愿违、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过失心态。
第二,黎某无证驾驶的行为虽然与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能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无证驾驶的司机都一定会出现致人受伤或死亡的结果。故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车辆应当作为量刑情节予以处罚,而不能作为定罪情节予以考量。
第三,本案交通肇事罪不具备转化为故意杀人罪的条件。交通肇事罪表现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置被害人于危难之中而不顾,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后因逃逸致使先前的受害人死亡。而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则是行为人故意使被害人失去了被救助的条件,因而致使其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又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丧失得到救助的可能性;又或者肇事后,被害人尚未死亡,但肇事者为了杀人灭口,再次故意将被害人撞死,或者当时其明知被害人就被拖挂在车下,但为了逃逸不顾被害人生死,将被害人拖挂致死。显然,交通肇事转化为故意杀人的典型特征就是要求加害人做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积极行为,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其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案中,黎某肇事后驾车逃逸,采取的是一种消极不作为的行为方式。且案发的地点在中心城区,黎某逃逸的行为也并未使得被害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期间也没有其他加害行为的介入。虽然最终导致王某死亡,但显然并非是黎某在故意创造条件,积极追求结果发生,这两者的行为模式差异较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案黎某的行为排除故意杀人罪。
2、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从概念上看,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过失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不特定的多数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为。
首先,黎某主观上不存在危害公众安全的犯罪故意。在排除故意方面,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在过失犯罪方面,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的过失心态针对的是可能造成交通事故的预见和判断。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加害者的过失心态针对的则应当是可能造成相当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并与之相当的公共安全的严重危害结果的预见和判断。因此,虽然是无证驾驶但不代表就一定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行为人对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心理不能苛求于上升到危害公众安全的层面,否则就明显加重了行为人的社会责任,而我国刑法也就没有必要再另行设立交通肇事罪了。
第二,就客体而言,我国刑法学界中的通说认为,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或者是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然而从犯罪侵害的直接客体进行分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公共安全。交通肇事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 主要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到重大的损失。从广义上讲,交通运输安全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但刑法把侵害交通运输安全的行为单独规定为交通肇事罪,这样看来,二者虽然存在竞合关系,但在此种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作为特别规定具有特定性,仅指侵害交通运输安全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关注的是一般性的公共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兜底条款,具有补充性和包容性,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的程度应与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具体危险具有相当性。在本案中,黎某未经过系统的驾驶培训,天黑降雨容易影响司机的判断能力,加之案发时受害人王某正跌坐在机动车道上,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最终导致王某被碾压死亡。而黎某在肇事逃逸后,虽然慌乱,但也没有发生其他的危害后果,上述犯罪情节难以上升到危害公众安全的层面。因此,本案应当认定黎某的行为危害了交通运输安全而非公共安全。
第三,就客观方面而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罪名并列规定在了相同法条中,且处以相同的法定刑。由此可见,“其他危险方法”是对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四种行为的兜底,根据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对这四种行为之外的其他危险行为要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应当要求该行为具有与这四种行为相当的危险性、破坏性,而不能泛指其他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如果对无证驾车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必须同时符合该罪的主客观条件,不能简单以危害后果判断无证驾车这一行为是否构成该罪。在本案中,黎某无证驾车仅仅是一种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并且,黎某不存在酒驾、醉驾等其他情节,虽有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但完全能够用交通肇事罪来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本案中,黎某的行为符合上述法条第二项的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出租车司机程某和保时捷司机黎某的行为都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法院一审判决对于罪名的认定是正确的。
作者:石磊
编辑:王晨伟
责编:郑黎波
主编:姚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