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18:12:15来源:法律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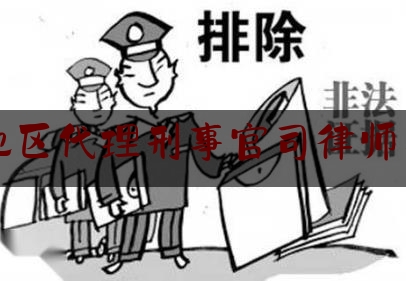
2020年12月4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受贿、行政枉法裁判、诈骗案,对被告人张家慧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根据张家慧受贿案的案情披露,有37人向张家慧行贿,其中律师达18名,发人深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检察官、法官与同为法律共同体成员的律师,在为了共同促进司法的公正,进行良性交往沟通的同时,又应该如何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的要求,自觉约束与规范彼此之间的接触交往行为。
在展开探讨之前,笔者想先澄清一下理念上的问题。在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每一位党员同志都要深刻理解和认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内在含义,尤其是从事司法的党员同志,在长期用法理思考,往返于案件事实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之间,早已形成固有的罗辑思维,在面对纪检监察机关对其涉及违纪的审查时,往往习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当事人,套用法理思维,理解认识党纪条规的要求。完全没有意识到党纪条规针对的特定对象是具有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员,而不是普通公民。这种自我认识的偏差本质上是一种党员意识在弱化的表现。作为一名党员,在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就已经承诺将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完成了自身权利的让渡与更高义务的加持,铮铮誓言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份契约,意味着每一位党员同志对自身行为将科以高于普通群众的注意义务,党规党纪正是以党员为规范对象、以义务为本位,监督每一位党员的强规范性模式,这充分体现在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证据认定标准的差异上。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党纪体现了最严的规范要求,反映在对定纪证据标准上较为宽松的“明确、合理、可信”标准,而刑法从保障公民人权的角度,反映在对定罪证据标准上严苛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可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两种要求。党员同志唯有增强党员意识,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遵守党纪条规的规定,清晰地认识到纪律的红线,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能够有明确的预期,避免触碰红线,从更高的层面讲,自觉内化为一种较高的党性修养。另一方面,凡事也需要辩证的看,党纪条规虽然对党员科以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其明确性也应当达到一定程度,这也是规范的基本要求,在制定、适用和解释过程中,为党纪条规划清合理的边界范围,避免在执纪监督时动辄上纲上线,不教而诛,影响党纪条规适用的效果与权威,达不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纪法情理贯通的目的,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对此,我们可以以“律师是否是检察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对象”这个问题为切入点,展开探讨。
让我们先看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涉及“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规定。根据《条例》对“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规定方式,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直接明示方式,如《条例》第九十条第一款:“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住房、车辆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第二种是间接方式规定,即条文中对特定抽象行为只原则规定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处罚要件,在实际执纪中,如果认定存在“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就能够认定“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要件的成立。如《条例》第八十八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如果党员收受的是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礼品、礼金等,就具备“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要件,进而认定违纪行为的存在。类似的《条例》还有第九十二条:“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此外,中纪委《全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中专门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作为专门的一类问题予以统计通报,《条例》中其实并无“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的直接规定,认定的依据其实是《条例》第九十二条:“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因为如果接受的是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就能推定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了。此外,还需要注意区分“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条例》之所以作此区分,在于前者的构成行为性质较之后者轻,对于结果的要求就相应的有所差别,前者“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应当是明确和具体的,对违纪行为的认定提出相应较高的证明要求,如《条例》第九十条第二款:“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其中也可能存在党员通过与管理和服务对象进行借贷等金融活动的方式获取大额回报的问题;后者“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主要立足于提前预防,抓早抓小,实际上降低了违纪的认定标准,将处罚端口前移。为此,“管理和服务对象”范围的界定直接关系违纪行为的认定,至关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权威机关对“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如何理解和界定的,笔者搜索了网络,目前可查询到的官方文章只有《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8年第23期的一篇文章“如何界定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财物的违纪行为”中提及对“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理解。根据文章内容,笔者提炼出作者界定“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观点:一是管理和服务对象具有相对性,取决于对应的公职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权限;二是管理和服务对象应当是受公职人员职权行使或职权影响范围内的人员。三是对于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认定,一般应从其所从事的业务是否可能或已经受到该公职人员职权的影响或制约,只要具备影响或制约的可能性,除非存在正当理由的反证,否则就可以推定为“管理和服务对象”。可见,界定“管理和服务对象”的核心是“其业务是否可能或已经受到该公职人员职权的影响或制约?”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管理和服务对象”可以存在广义、中义、狭义三层理解,广义的理解:只要某个单位被赋予的职权中有可能影响或制约相对方业务的,那么这个单位中的所有公职人员与相对方都存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关系;狭义的理解:某个单位的公职人员履行的职权必须已经具体的影响或制约到了相对方的业务,这个公职人员与相对方才存在“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中义的理解:某个单位的公职人员履行的职权只要存在影响或制约相对方业务的可能性,就可以认定存在“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由于广义的理解过于泛化了“管理和服务对象”的概念,容易导致打击面过大,影响纪法效果,尤其对检察院、法院这类司法机关而言,职权性质与行政机关存在较大差异,而检察院的职权范围相对于法院更有限;而狭义的理解又过于保守狭隘,不利于抓早抓小、提前预防效果的发挥,唯有中义的理解具有相对合理性。不过,同时还要处理好“可能影响或制约”与“已经影响或制约”、“单位中行使具体职权的公职人员”与“单位中所有公职人员”的关系,这些都需要结合发生的具体情况予以综合把握,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回到“律师是否是检察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问题,既然“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界定有赖于公职人员职权对相对方的影响或制约判断,那我们先看看检察院究竟拥有哪些职权。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一)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二)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三)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四)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五)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六)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七)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八)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既然管理和服务对象具有相对性,取决于对应的公职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权限,那么履行上述不同职权的检察人员,对应的管理和服务对象也会不同。上述检察院履行的职权当中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最主要的,集中在第一至第三项的职务犯罪侦查、刑事案件批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等职权,会给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业务带来影响或制约;第二类是较为次要的,集中在第四、第五、第六项的公益诉讼、诉讼监督、执行监督职权,可能会影响或制约代理了当事人申请诉讼监督、执行监督的律师业务,但此种情况并不多见;第三类是较为少见的,即第七项对监管场所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职权,对于代理了当事人举报监狱、看守所执法活动涉嫌违法的律师具有影响或制约。结合前文的阐述,我们不能用广义的理解,简单地把所有检察人员与律师看成是“管理和服务对象”。与此同时,对于检察人员承办的具体案件的代理律师,毫无疑问可以认定为“管理和服务对象”,两高三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明确做了相应的要求。那需要探讨的就是没有代理具体案件的律师与履行相关职权的检察人员如何确认是否是“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笔者认为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判断的核心是要围绕“检察人员履行的职权是否会对律师业务产生影响或制约”的标准来判断,同时考察检察职权与律师业务联系的概率。对于上文划分的检察院职权中第一类职权,主要涉及刑事案件,显然会对业务包含刑事业务的律师产生影响或制约,而且此种影响或制约对于检察院来说是较为常态化、多见的,对于易发的廉政风险具有提前预防的必要性,可以确认这类律师与检察院履行自侦、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职权的检察人员(包括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和检察长)存在“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应当注意遵守相关禁止义务。对于上文划分的检察院职权中第二类、第三类职权,考虑到检察院这类职权与律师业务的关联度并不紧密,且并不常见,影响或制约有限,对于“管理和服务对象”倒是可以采用狭义的理解,在与律师业务有具体案件关联的时候,再确认“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几点问题:
第一,如果某位律师代理了检察院的具体案件,那么这位律师就是这个检察院的管理和服务对象。这个检察院的所有检察人员与该律师都存在“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包括具体承办检察官以外的检察人员,如法警、办公室、政治处、行政后勤保障等部门的检察人员。《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就是防止上述人员干预司法办案,也间接说明上述人员是可以通过打听、过问、干预具体案件办理间接影响律师业务的。但是如果律师没有在检察院代理任何案件的情况下,就不能做上述类推。
第二,当检察人员与律师存在除“管理和服务对象”之外的角色冲突时,如系亲属、同学、朋友关系时,仍然要在这些角色中把履行检察职权这个公权力的角色摆在第一位去思考如何接触交往,审慎行为,这不仅是对司法公信力的自觉维护,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第三,确定“管理和服务对象”关系只是评价违纪行为成立的要件之一,还需要综合其他要件综合判断违纪行为是否成立,如“宴请”、“礼品”、“礼金”等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