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5 10:53:12来源:法律常识

“前浪”“后浪”正在逐渐占据话题榜的时候,鲜有人留意到“中浪”们正在经历什么。30岁的赵子健就是一朵“中浪”,他曾满怀热望来到北京打拼,偿清债务,开启了崭新的职业履历。然而疫情影响的当下,他成了最先受到冲击的人,被公司辞退。他失去了力气,不再尝试新找工作,而是直接从北京退场。

2020年4月,30岁的赵子健决定离开北京。
最后一次见面时,赵子健正在马路对面打电话,他挥挥手,示意我跟上。许久没见,他清瘦不少,背影看上去还像个少年。我们隔着半米距离朝单元门走去,他挂掉电话,冷不丁冒出一句:“我家现在乱得跟猪窝一样,你别嫌弃。”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跟在后面,乐呵呵地回道:“没事儿,就当我瞎了吧。”
一小时前,赵子健发来约饭微信,我当是一次寻常酒局,抓起手机,趿拉着鞋直奔他住的小区。可当他拉开一居室的房门,我发觉事情有些不对。
客厅一片昏暗,餐桌上外卖盒排成了队,吉他被扔在沙发旁边,落得一身灰尘,卫生间里厕纸堆得快要溢出来。赵子健一向最爱干净,眼下屋里居然乱得无处下脚。
我有些尴尬,到卧室寻了张干净椅子坐下,他随手递来一罐可乐,宣布了离开的决定。
空气安静了几秒,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认真地指着四周的木质家具,“你看看还有什么能带走,这些桌子、椅子、落地灯都是我买的。”
这几年,朋友们但凡心情不好,都会嚎上几句“我要离开北京”。但那些大喊着“受不了,要离开”的人往往不会启程,反而像是恋人在对北京撒娇。真正的告别是静悄悄的,有时一觉醒来,看到朋友圈里多了几张机场、火车站的深夜留念,一段故事就默默画上了句点。
可赵子健,我一直觉得他是那种要用一辈子和北京缠斗到底的人。
见我不吭声,赵子健开始在屋里四处搜罗能留给我的“遗物”。出租屋里带不走的物品都给了朋友,衣柜顶上孤零零地躺着只黑色登山包,等待主人将它填满。在这座城市待了六七年,赵子健打算带走的物件寥寥。窗台上的米奇玩偶沾满了猫毛,他说:“两只都送给同事了。”像是替自己开脱,又补了一句:“都是捡来的流浪猫,它们会习惯的。”
最终,他扔来两包抽剩下的薄荷烟,一本没开封的书。我捡起来一看,打趣道:“这是暗示我们都是北京的《局外人》吗?”他笑了笑,又扔来一支录音笔,同时打开了电脑。
屏幕上四段长长的的音轨,标记着劳动仲裁的字样——受疫情影响,赵子健工作的公司经营状态不稳定,向他提出解约,却没给合理赔偿。他就这么被甩出正常轨道,突然有了离开北京的打算。
燃剩一半的香薰蜡烛被拽过来当烟灰缸,气氛变得有些压抑,我们决定不再深聊,出去找个饭店喝一杯。临走前,我看了看门厅挂着的小黑板,上面写着:今日晚餐,青菜拌面。字迹已经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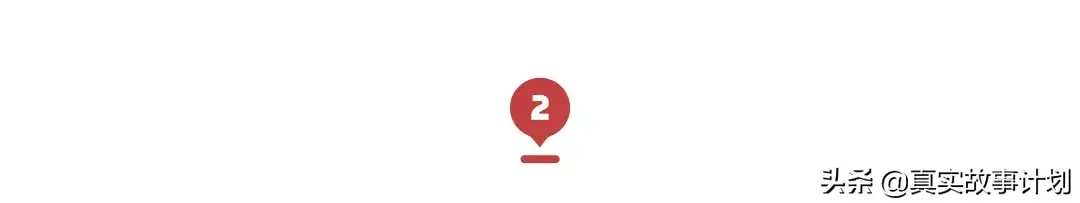
赵子健是为还债来到北京的。二十出头时,他在外地做生意欠下八十万外债,之后独自飘荡到北京,白天做三份工作,晚上在青旅里没命地喝酒,一边奋力还债,一边任由自己醉倒在地。
北京没有辜负年轻时的赵子健,进入正兴盛的互联网行业,凭着一股拼命劲儿,两三年间,他还清欠款,从地下室搬进合租房,初步融入了这座城市。
我和赵子健相识在2016年最后一天。那时我19岁,趁寒假来到那家青旅做义工。他26岁,刚还完欠款,换了更高薪的工作,时不时会回青旅住上几天。
那天晚上七点,我补完觉,迷迷糊糊地走进旅社厨房,就看见赵子健正在盛一盘大虾。他倒是自来熟,都没问我是谁,伸手指挥我去旁边坐,等着吃饭。
刚到陌生环境,那顿饭我吃得很拘谨,时常接不上周围人的问话。他坐在一旁帮我岔开我接不上的话题,还不停招呼我多吃点。这让我对接下来的义工生活有了些期待。
北京冬天透着股肃杀,街道上行人缩着脖子快速穿行,地铁口里人潮和风同样拥挤。相比之下,青旅热闹喧哗,六十元住一晚的床位,被一茬茬新北漂当作起点。
当时,和我同住一屋的一个女孩为了留在北京,包下一张床铺,连着面试了一个月,每天订一盒外卖,在屋里边吃边修改简历。有次改到崩溃,她抬头冲着对床素不相识的游客大哭道:“我是不是真的不行?”第二天一早又收拾好电脑,踏上公交。
有位中年大叔常坐在大厅沙发上喝酒,喝到兴起,逢人便讲他离婚的往事,和东山再起的宏愿。还有一个被考研逼到崩溃的富二代,瞒着家人跑到北京找工作,住便宜旅店、吃日料外卖,周围人都笑他,“有钱人的北漂,可以称之为北伐。”
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没什么生活与求职压力,自然不懂大家为何如此拼命。不用工作时,我在二环的胡同里随意游荡,赵子健总站在胡同口抽烟,为了与他接近,我也学会了吞云吐雾。
熟悉之后,我才知道他对青旅里新一波年轻人真是不错。青旅里有个整天聊着电影梦的女孩,他被女孩的说辞打动,听着听着就送了对方一台相机,没要任何回报。有人哭诉找不到工作,他也搭着人情联系朋友帮忙内推。
他像是青旅里的圣诞老人,派发着礼物,帮一波波新人寻找机会,偶尔做上一桌海鲜,招呼大家吃饭,轻易地聚拢了人气。
正是因为赵子健,我才下定决心也要留在北京。因着在青旅的见闻,这座城市在我心中被蒙上了一层温情面具。当时我只觉得,北京可真好啊,只要努力,谁都有权利留下,没人会问来处与归途,说出口的梦想也不会被嘲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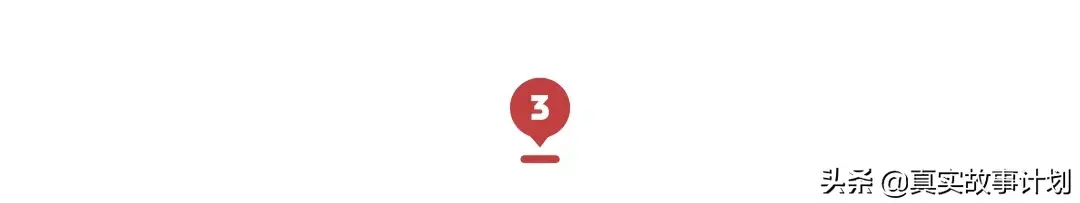
2018年,我回到了北京。从城市的围观者转为亲历者,生活突然变得粗砺起来。我做着日薪50元的实习工作,将房子租在顺义,每天转三趟地铁跑去朝阳区国贸上班。
漫长的通勤路走上几遭后,我才逐渐意识到那些客人在青旅之外的真实生活,多的是我看不到的艰辛。现在的我不过是在重复那些客人的命运,北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挑战者,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要用梦想填饱肚子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再次见到赵子健是在望京的烧烤摊上,我换了家新的实习单位,日薪涨到70元,还是觉得人生无望,特意约他出来聊天。
夏日夜晚的烧烤摊承载了无数豪言壮语,几杯啤酒下肚,平日里藏好的矫情话又冒了出来,我说起来北京的初衷,是希望永远踏实地写文章。
他扔下烤翅,抬头直视着我的眼睛说道:“知道今日头条吗?现在都是大数据推荐,写得再好,谁还有心思看几千字的文章。”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心想,当初在青旅你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他谈起最近的日子,从互联网大厂跳到一家创业公司,选了很有发展前景的视频领域,经常出差半个月,回公司后再连轴转。他不再顾得上去青旅过周末,除工作之外的生活一片空白,连飞机杯都用一次性的。
我听得没了胃口,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们一起沿着街道往他公司走,我不想再谈工作,他却一直重复着“努力,选择,机遇”。最后还承认,腰疼得过分,为了挤时间锻炼,都从住处慢跑去上班。
到了公司,已经快凌晨一点,他打开电脑继续修改视频。最后一步完成,他把我的椅子拉到巨大的屏幕前,得意地递来一只耳机。
视频拍得高端精美,背景音乐卡在画面上分秒不差。我盯着屏幕有些走神,觉得没见面的这两年,赵子健不再是那个刚从泥潭中挣脱,对所有人的梦想都满怀兴致的男生,他似乎改了方向,要在这座城市过更安稳的生活。
回家路上,出租车司机将四面窗户全打开,货车在一旁呼啸而过,飞速碾压路面上的石子。我顺手点开微信里几个久未联系的头像,当初立志要留在北京的女孩漂去了上海,想东山再起的大叔已经在长春开了两家酒吧,而富二代的确在北京找到一家不错的单位,只不过单位在北京,他本人被派去了非洲。
我替赵子健欣慰,虽然他不再是那个对别人的梦想感兴趣的年轻人,北漂五年,他好歹稳稳地踏进了上升通道。
之后的日子,我们没再见面,每次相约吃饭,不是他在外地出差,就是我在熬夜工作。一次半夜三点,我结束赶稿,给他发去微信哭诉,他立刻秒回:加油。我笑他手机长在手上了,他淡淡地回了两个字:加班。
2019年中秋假期,我们总算相聚,他意气风发地讲起接下来的出差行程,我以为像他这样停不下来的人,会一直留在这里,和北京相互塑造着向上生长。没想到第三次见面,即是离别。
事情其实向我露出过端倪。半个月前他向我打听是否认识律师,一周后我跟他抱怨工作出现问题,他一改常态,不再鼓励我,而是颓然地回了句“谁的北漂不这样”。两天前他又在朋友圈里送书,我还以为他只是要搬家。
从赵子健家里出来,走进饭店,他又恢复了四年前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话题绕来绕去,就是不提究竟为何离开。我跟他说些烦恼,他也只是笑笑不搭茬。
一顿饭吃完,他翻起锅里的烤鱼,看着我说:“你知道鱼什么地方最嫩吗?是鱼鳃下面这块肉,因为它不需要用力,从没受过折磨。”

吃完饭,他提议到家附近的酒吧坐坐。他在这里住了两年,想来已是这家酒吧的熟客。到了店里,他轻车熟路地跟服务员打了招呼,又要了几瓶啤酒。喝到有些微醺,主动谈起了离开的原因。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2020年春节放假,他开了几千公里的车回家,路上还在计划着节后的工作安排。等再开回来,面对的却是一桩劳动仲裁。
疫情之下,公司决定裁减收益不多的部门,找借口“优化”了赵子健。他买了只录音笔藏在兜里,一遍遍地跟hr、劳动局交涉。过程并不复杂,但事情结束后,他在家待了半个月,瘦了20斤。
我既难过又不解,不停追问他:“换个工作不就好了?也不至于就这么离开啊。”
他叹了口气,晃了晃手里的酒杯,说道:“人到了30岁,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我28岁前从不骂人,这两年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说脏话。”
痛苦是一点点累积升级的。他说起前些年刚到北京时负债累累,为了还钱能没日没夜地拼搏,解决了欠款,又甘愿为更好的生活环境付出青春。
在创业公司,他承担着巨大的工作量,和同事去西藏出差,所有人都高反了,他自己赶完了四五个人的拍摄任务。他没有抱怨地做着这些,以为埋头工作就会有回报,可眼见着就快要兑现成果的时候,资本撕下笑脸,一张解聘书又让过去两年的努力化为乌有。
眼下他30岁,在北京却还是没有安定居所,连一开始赖以慰藉的工作价值感也消失殆尽。这次离职让他觉得,北京拥有着一茬茬年轻人的青春,却安放不下所有人的下一阶段人生。许多人最终要离开,他决定让这件事来得更早些。
听着他的焦虑,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为了身体健康,赵子健许久没碰烟酒,见我一根接一根地抽,他掏出电子烟吸了两口,呛得直咳嗽。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语无伦次地劝他留下来。
赵子健听着我絮絮叨叨,一句话就堵住了我:“你不明白,30岁了,再过几年去应聘,我说我多能拼,谁信呢?”我才23岁,不懂他为何悲观成这样,但还是住了口。
北京的故事没什么新意,却总是很刺激。一场疫情之后,游戏难度加大,写字楼里人流明显减少,各类公司无差别地承受着影响,用裁员暂时抵御危机,有些干脆倒闭。许多失去工作的人,被迫退出北京。
酒吧里客人不多,邻桌年轻的女孩叫嚷着:“我妈说我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还不如回家,我就不回去。”灯光下,赵子健眼睛红红的,低头时,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他给朋友打去电话,准备再组一场酒局。已经结婚的朋友无法再在深夜赴约,他笑着跟电话里的人说:“我要离开了,13号就是deadline,见我,抓紧。”
我知道再也留不住他,只告诉他:“跟你聊完,我也想收拾行李回家了”。他盯着我的眼睛,慢悠悠地说道:“你不会的。你明知道这里有多难还是来了,这话还是等你30岁以后再说”。
临走前,他晃晃悠悠地走去前台,把最后一点“遗产”——十几罐猫罐头留给了酒吧老板。
- END -
撰文 | 姜念
编辑 | 温丽虹